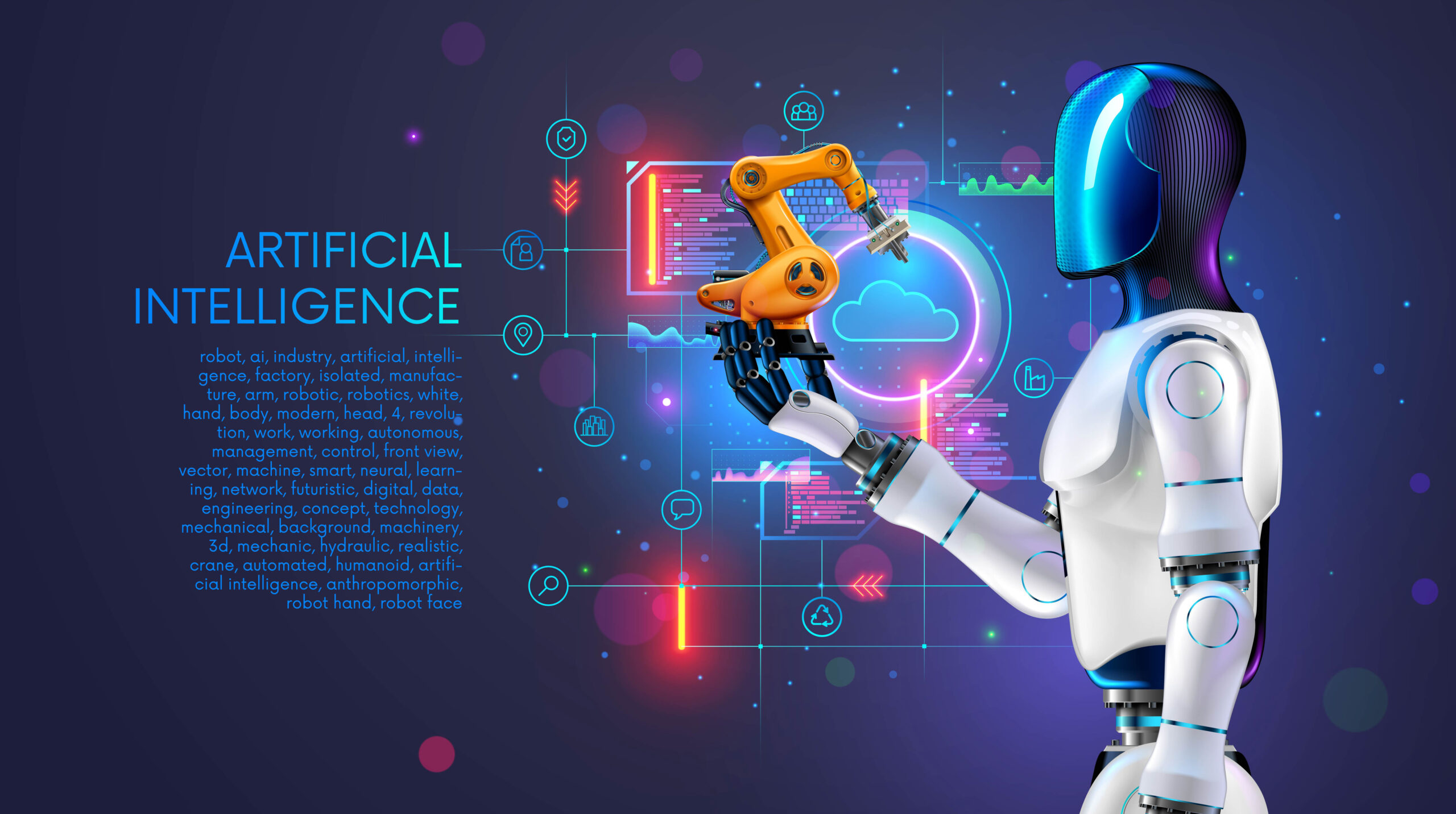隨著利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 AI)提供音樂創作服務的APP越來越廣泛,甚至有公司特別舉辦AI音樂創作大賽來推廣APP使用。對於這些使用AI APP工具創作音樂的使用者而言,即使透過APP工具創作出有商業價值的音樂,其能否因此獲利仍主要取決於著作權的歸屬認定。本文意在透過以往傳統流行音樂的創作經驗,來探討目前改為使用AI APP輔助的音樂創作者如何取得著作權人身分的議題。

歌詞發想過程
傳統歌詞創作常有「故事」作為背景,例如以下三例。首先,〈大齡女子〉一曲的創作者 — 陳宏宇表示其在創作該曲副歌歌詞第一句「女人啊,我們都曾經期待,能嫁個好丈夫」後,以該句出發而為「歌手的背景進行鋪陳」,例如「她經歷過什麼」、「為什麼要說這句話」,而漸漸形成一段故事並呈現在主歌中[1]。陳宏宇認為「那些溫暖、療癒之類的形容詞,必須真的符合歌手本身,才能夠打動人心」。
再者,三立新聞台主播張齡予於創作〈阿爸〉一曲時的心情是「如果一生只為一個人寫歌,想要寫給爸爸一首歌」[2]。因而,〈阿爸〉歌詞的「意境跟靈感來源」為在宜蘭往返台北的雪山隧道未通行之前 — 「在宜蘭飯店工作的張齡予爸爸為了趕回台北照顧小孩」而「不辭千辛萬苦每天搭火車四小時通勤」、「雖然很累但是想到小孩笑臉,他堅持了十年」、「那份對子女堅持的愛到現在還是讓人記憶猶新」。
最後,第31屆金曲獎最佳作曲人獎得主余佩真提到得獎歌曲〈昏你〉是為了朋友結婚所創作;當時其擔心「朋友與交往沒多久的對象要閃婚」,但「又希望他可以得到幸福」;為了寫歌,其上網爬文找到「多年前在台灣轟動一時的『小鄭與莉莉』的姐弟戀」,並發現很多輿論資訊,而後才有了「寫歌的靈感」[3]。
歌曲靈感來源
傳統歌曲創作也常會以主題為基礎。例如林欣彥,著名創作作品為〈Funky那個女孩〉[4],曾提到其作曲時不是漫無目的,而是「感覺來了同時,將主題先設定好」;假設感覺在下雨天發生了,「他會先將主題定調在『天氣』」以避免創作發散,而「緊接著就會將這樣的情緒、氛圍延伸」來創作和弦,而在和弦的選擇和編排亦採相同概念進行;在「有個大概的基底後,通常在三個小時內就會把曲子寫完」[5]。
此外,作曲者為掌握作品的曲風,必須參考許多相關音樂著作。例如音樂製作人兼詞曲作者林尚德表示自己「很喜歡去研究過去成功的案例」,而對「那些寫得很好、大家很喜歡的歌曲」,探究「到底有什麼值得學習的地方」[6]。詞曲作者呂孝廷也曾指出在「歌曲製作過程中,我的工作流程通常會先聽Reference,包含收歌訊息提供的、以及我自己找到覺得合適的歌曲」[7]。
使用AI APP音樂創作之問題
假設在使用AI APP進行音樂創作,歌詞的文句建議與歌曲(或編曲)的旋律回饋皆基於使用者對音樂風格的選擇,後再由APP所產生。因為APP沒有創作的思考過程,而僅是呈現機械式的電腦程式運算結果,故與傳統的音樂創作過程有相當的差異。然而,若歌詞為使用者的原創,則此類似於傳統的音樂創作情境,而可能有創作發想過程的存在。
舉證責任的考量及實際侵權案例分享
假設APP使用者之創作因具有原創性而成為著作權法所保護的音樂著作,但問題是著作權人如何舉證創作過程?依據《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1671號民事判決》指出雖「我國著作權法係採創作主義,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但「著作權人所享著作權,仍屬私權,與其他一般私權之權利人相同」,故「對其著作權利之存在,自應負舉證之責任」。因此,「著作權人為證明著作權,應保留其著作之創作過程、發行及其他與權利有關事項之資料作為證明自身權利之方法」,以利「如日後發生著作權爭執時」,能「提出相關資料由法院認定之」。
具體而言,在訴訟上,著作權人於舉證時至少應證明下列事項:
(1)著作人身分:藉以證明該著作確係主張權利人所創作,此涉及著作人是否有創作能力、是否有充裕或合理而足以完成該著作之時間及支援人力、是否能提出創作過程文件等。
(2)著作完成時間:以著作之起始點,決定法律適用準據,確定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3)係獨立創作,非抄襲,藉以審認著作人為創作時,未接觸參考他人先前之著作。
另《著作權法》第13條規定「在著作之原件或其已發行之重製物上,或將著作公開發表時,以通常之方法表示」以下事項,有推定該些事務為真效果:(1)以「著作人之本名或眾所周知之別名者」表示著作人;(2)著作發行日期;(3)著作地點;(4)著作財產權人。該規定係為「著作權法為便利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之舉證」所設計。
然而,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仍有積極舉證之必要;特別是當著作未公開發表的時候。在流行音樂創作的情境,以《智慧財產法院(智財法院)106年民著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第7號案)為例,原告主張被告抄襲其創作〈下輩子〉(僅有歌曲)並以〈後世人〉為歌名收錄他人公開發行的專輯中;但原告的作品未曾公開發表,而僅是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給被告參考。
智財法院指出第7號案原告欲「主張其為系爭歌曲之著作權人,自應舉證證明著作人身分、著作完成時間及獨立創作等事實」。根據承辦法官之調查,原告有作曲的學經歷,因為原告具音樂相關學系的學士學位、並曾實際於公開發明的專輯中參與某歌曲的作曲與編曲。其次,原告於2012年11月14日創作完成〈下輩子〉時即聲音檔案寄給被告,並陸續寄出相關旋律修改檔案給被告。最後,儘管無原告創作思路的資訊,智財法院仍認第7號案〈下輩子〉「為其獨立創作」且「未抄襲他人先前之著作」,故「應受著作權法保護」。
另以《智財法院109年民著訴字第25號民事判決》(飛兒案)為例,錄製試聽版(demo)並搭配作詞人或作曲人之證詞,亦是證明創作的方式。該案涉及三首音樂著作 — 〈蒼穹〉、〈河畔〉與〈神曲〉之歌曲是否由「飛兒樂團」之創始成員 — 被告詹雯婷(藝名:Faye)、和兩個原告黃漢青(藝名:阿沁)與陳建寧等共同創作。
被告主張系爭三首歌曲為其所單獨創作;例如被告指出〈蒼穹〉之歌曲於創作時有錄製哼唱版的聲音檔案,而作詞人亦作證其從被告處收到該聲音檔案,並於聆聽被告陳述歌曲創作時之想像與由來後,才進行填詞。另方面,因原告無法舉出共同創作後的demo;另其所提出的證人僅能佐證demo「可能」同時被創作者和製作人所持有。因而,智財法院認為飛兒案的原告無法證明有共同創作〈蒼穹〉的事實。
註冊登入之形式
假設在使用音樂創作AI APP時,系統要求使用者必須註冊登入;而註冊時必須填入姓名、電子信箱、與手機號碼等資訊。如果此AI APP的系統有記錄使用者著作的聲音檔案,則其在搭配註冊者資訊之情況下,只要能落入《著作權法》第13條所規定「以通常之方法表示著作人之本名或眾所周知之別名者」,應可享有著作人或著作權人推定之效果。
其次,假設AI APP使用者操作到最後會將創作資訊(包括創作者名字及版權資訊)從APP上傳到區塊鏈平台,再搭配區塊鏈來記錄日期,則可能佐證著作人身份與創作日期。不過,若APP的操作介面並無顯示創作日期的資料,則舉證之相關資訊完整性不無疑問。最好是APP的系統有儲存創作日期之功能,以利於使用者取得著作權或著作人身分之客觀證明資料。假設APP提供使用者分享其成果至社群平台之功能,例如按下「儲存」鍵後會提供「分享」鍵,且該分享功能是一直存在著。因此,當創作完成後,使用者能即時分享相關創作至社群平台,以利用該平台的日期來記錄創作完成日。
最後,關於創作歷程,因現行APP的技術創新所標榜是提供讓不會音樂理論的人士也能進行音樂創作。因此對於「著作人身分」之舉證事項的要求應有別於傳統以「人」為中心之要求,亦即「著作人是否有創作能力」或「是否有充裕或合理而足以完成該著作之時間及支援人力」等問題,皆因APP的輔助而不再重要。至於「是否能提出創作過程文件」之問題,假設APP能記錄使用者如何選擇旋律或歌詞、如何調整旋律等,則創作過程之資訊即能提出,而有助於佐證著作人或著作權人之身分。
備註:
- [1] 歌詞創作面面觀:填詞人如何在流行音樂產業求生存?Blow吹音樂,2025/7/16
- [2] 主播張齡予跨界歌手 歌詞藏「父愛」做公益送暖‧ETtoday星光雲,2021/3/4
- [3] 金曲獎/余佩真爬文找靈感 轟動全台「小鄭與莉莉」助攻抱回金曲獎座‧ETtoday星光雲,2020/10/3
- [4] 【專訪】遊走在獨立和主流之間:剃刀蔣與米奇林‧Blow吹音樂,2019/8/15
- [5] 專訪米奇林/從詞曲創作到編曲,那些膾炙人口的歌曲是怎麼來的?Mag加點音樂誌,2018/10/24
- [6] 專訪金曲製作人/金馬配樂家 林尚德 -寫歌祕訣&迷思破解大公開‧大禾音樂製作,2019/12/30
- [7] 獨家揭曉!一年賣出40首歌的創作秘訣,R&B 編曲新銳呂孝廷老師專訪‧大禾音樂製作,2019/10/17
責任編輯:盧頎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