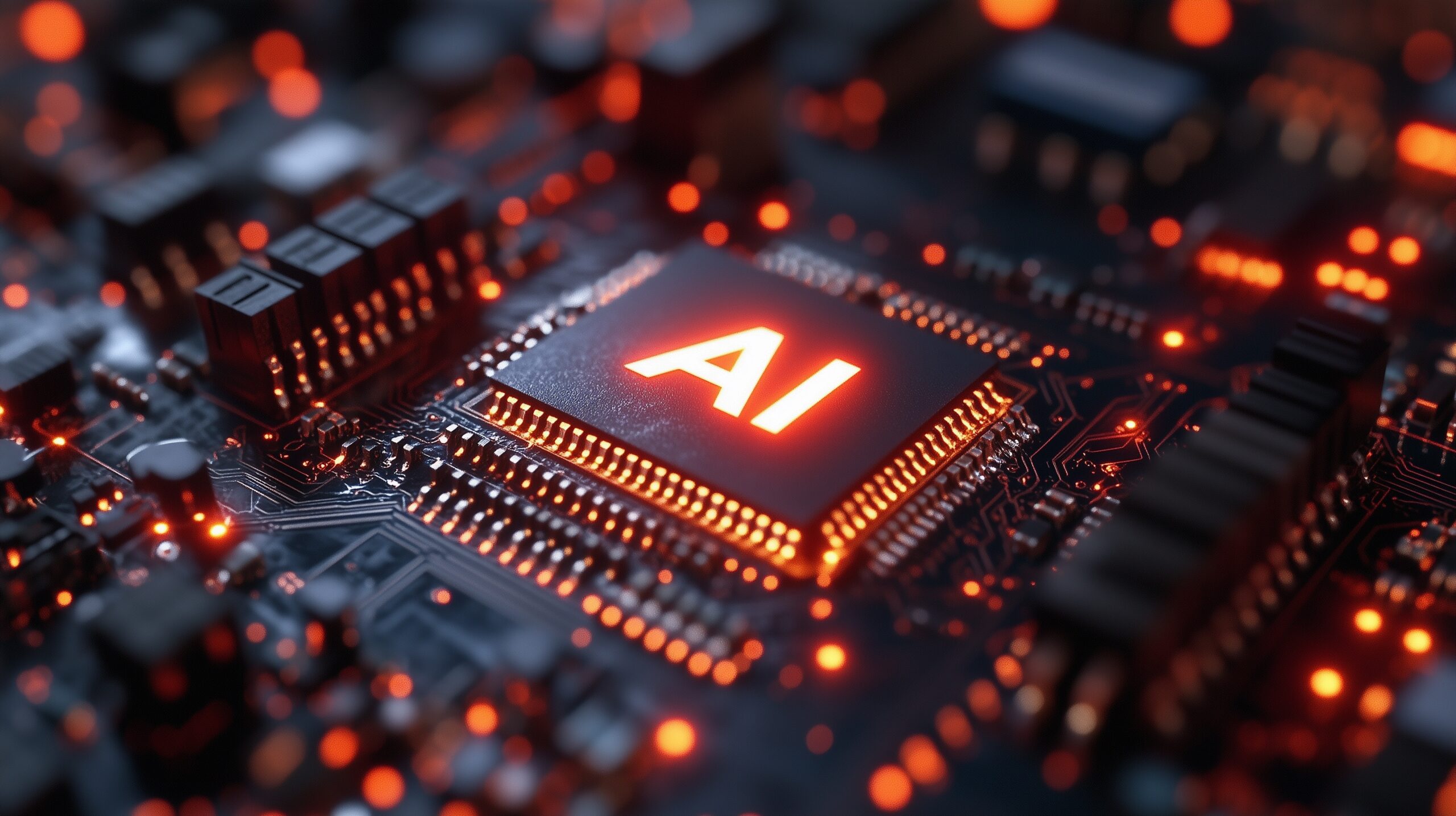假設提供人工智慧(AI)服務的公司(下稱AI公司)建置AI著作資料庫,而使用者在利用上述AI服務完成其著作後 — 對於最後的完成品,AI公司能否有《著作權法》上的保障?本文欲討論的關鍵問題是,使用者使用AI服務進行著作生成的過程能否讓AI公司有機會成為共同著作人,進而分享著作權?
情境假設
假設AI公司開發的APP可讓使用者選擇資料庫內AI進行著作生成,以AI編排或修飾而得到著作。若編排或修飾的行為達到原創性的程度,上述著作即受《著作權法》所保障。
「著作人」定義重整
《著作權法》第3條定義「著作人」為「創作著作之人」,但卻在第11條與第12條規定雇用人或出資人可和實際創作者約定由雇用人或出資人取得「著作人」地位。因為「著作人身分」的取得無關於「著作人」是否「實際」參與創作著作,「著作人」對於著作是否具有「原創性」之「具體貢獻」應非認定「著作人身分」時所必要考量。
此外,在雇用人情境中,受雇人以「完成」與工作相關的著作。在出資人情境,雙方承攬關係而使受聘人「完成」所約定著作。「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著作」或「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等,「完成」主因是雇用人或出資人所啟動的創作行為。
因此,認定「著作人身分」時,僅考慮其是否「參與」[1]完成著作即可。不過,若此「廣義著作人」欲主張著作權保障時,仍應證明其著作整體上原創性、對著作完成有資源的投入(即聘僱或出資),才得成為「受保護著作之著作人」,即「狹義的著作人」。
「共同著作人」認定
《著作權法》第8條定義 — 「共同著作」為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且其各人之創作屬不能分離利用者。判斷上,根據《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14號刑事判決》,權利人必須證明:(1)「須二人以上共同創作」;(2)「須於創作之際有共同關係」;(3)「須著作為單一之形態,而無法將各人之創作部分予以分割而為個別利用者,始足當之」。
從前述「著作人」的定義,本文提議新的「共同著作人」認定方式 — 即只要是參與創作者即可為共同著作人。但創作「參與」必須到達「表達」的程度而不是「概念」的提供,以符合《著作權法》保護表達的目的。
從此觀點,由於使用者著作係產生自AI生成著作,即使該著作不具原創性,但此著作的「著作人」仍能成為使用者著作之共同著作人。下個問題則是,AI生成著作的「著作人」是AI軟體、或其撰寫或訓練者、或是AI公司?
與「原創性」切割
如何在AI生成著作不具原創性的結論下,仍能讓AI公司成為「AI生成著作之著作人」。事實上,智慧財產法院於《106年度民著上字第10號民事判決》中,認定無證據可佐證系爭電腦軟體著作具原創性,但仍指出原告因僱傭契約而取得系爭著作之著作權。
同一件著作無論是否具原創性,在目前的制度下是於不同訴訟中各自認定;亦即,儘管D著作在A1訴訟中被認為有原創性,但A2訴訟之法官可能會認為不具原創性。無論如何,既然於A1訴訟中,原告Q被認定是著作人或著作權人,則其提供於A2訴訟中以相同著作提告之正當性基礎。
這樣詮釋制度目的在於使共同著作人認定遠離個別著作人所貢獻部分的「原創性」問題。因此,AI生成著作雖因其由AI軟體所生成而不具原創性,卻不影響著作人之存在。
進一步,AI公司可透過以下兩種模式成為使用者透過AI生成著作之共同著作人。
模式一:職務上之著作
關於AI生成著作,東吳大學法律系老師林利芝主張[2]應將著作人身分給予軟體設計者和軟體使用者,並傾向二者間擇一授予。
解釋上,AI公司應能透過僱佣關係而從AI生成著作之原始著作人(軟體撰寫者或AI模型訓練者)上取得著作人身分。問題是,AI公司和軟體撰寫或訓練者間無論公司有無負擔勞、健保,都能成立僱傭關係。
參酌最高行政法院於《103年度判字第567號判決》指出「僱傭關係乃指受僱人聽從雇主指揮」,其「本身不負盈虧及任何成本」,並「為雇主提供勞務而支領雇主所支付報酬」。判斷上有四個考量因素:(1)人格上之從屬性、(2)親自履行之必要性、(3)經濟上之從屬性、及(4)組織上之從屬性。
由上述案例,面對醫院主張其與主治醫師間屬「委任關係」,最高行政法院認為主治醫師在組織上與人格上皆從屬於醫院,致兩者間具有上下隸屬之關係,因而存在僱佣關係。
理由包括:(1)醫院提供護理人員、醫療器材、場所租金、及其他營業成本支出,但主治醫師除免負盈虧風險外,還有最低收入保障;(2)醫院對主治醫師有管考出缺勤之權利,例如有請假規則,用以規範主治醫師,且相關規定修改時,其生效無須知會主治醫師或讓主治醫師參與和同意;(3)醫院顯有一定能力掌控主治醫師的收入。
同理,AI軟體撰寫或訓練者只要是在AI公司內獲得行政支援、使用包括電腦與網路研發資源、遵守上班出勤規定(包括彈性工時或遠距工作)、及支領固定薪水或獎金、或其他工作報酬等,則應認為有僱傭關係。
因此,AI生成著作理應為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例如其受雇目的為開發AI音樂創作軟體與APP。若有依《著作權法》第11條約定雇用人為著作人時,AI公司即為AI著作的著作人,進而可行使以上同法第16條之「姓名表示權」,而要求於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列名AI公司為著作人。
模式二:契約關係
即使AI軟體撰寫或訓練者仍為「著作人」,AI公司可透過契約方式要求軟體撰寫或訓練者同意以「AI公司」標示著作人。
參酌德國法院的Irene von Velden案判決,其處理出版社和不同作者間約定系列叢書的統一筆名問題[3]。審理Irene一案的法院維持約定有效性,因為系爭筆名「不具有標示創作人姓名功能」而僅代表該特定的系列叢書,故系爭約定雖要求作者放棄標示其本名或筆名的權利,但未打斷作者與其作品關聯性程度,且未涉及姓名表示權之核心範圍(即著作人身分之確認)。
Irene案判決適合用於著作人標示之思考。首先,假設以APP名稱為著作人標識,雖然將其標示於作曲者下,可理解是表示音樂著作係利用該APP所創作。再者,AI生成著作既然是電腦軟體的運算產物,故一般人會認知有AI生成著作的前身AI軟體之存在。而AI軟體必然有其撰寫或訓練者,故APP名稱標示無法抹去軟體撰寫或訓練者之存在,因而未切斷二者與AI軟體或AI生成著作間之關聯性。因此,約定以APP名稱標示於作曲者下,不會干擾姓名表示權之性質,而屬有效約定。
以APP名稱標示著作人
基於訴訟上考量,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標示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是必要的,因為根據《著作權法》第13條有推定效果。不過,推定是可推翻。
使用者著作之「著作人」情況有:(1)使用者與AI公司;(2)使用者;(3)使用者與AI軟體設計或訓練者。
在不同的情況下,將APP標示為著作人有不同的意義。在第一類中,AI服務公司行使其姓名表示權而以APP為著作人稱呼。第二類與第三類會涉及對使用者、和AI軟體設計或訓練者的姓名表示權限制,但該標示表彰相關著作係利用APP所創作。雖AI公司依使用契約或僱佣契約獲得著作財產權,但以同時標示著作財產權人為佳。
建議與結語
當今政府對AI政策的討論,缺乏「將著作權的保障授予AI所生成的著作」課題,而忽視涉及人類行為互動之使用者著作。
市場上已存在提供AI輔助流行音樂創作之服務,而相關公司就該服務的商業模式有著作權保護之需求。因為軟體設計或訓練者是AI軟體產出AI生成著作之控制者,則AI生成著作之創作者即為該設計或訓練者。進而,AI公司因與該設計或訓練者間為僱傭關係,且相關AI生成著作乃履行職務之成果,而讓AI公司成為「著作人」。
因此,如何在以保護自然人創作為目的之《著作權法》體制下,考量相關的司法判決,以制訂特別保護機制,是智慧財產局作為主管機關應正視的課題。
備註:
- [1] 此處的「參與」是指實際創作、與聘僱或出資請他人創作。
- [2] 林利芝,著作權決戰AI畫作-論人工智慧時代的藝術智慧在著作權法上之評價,中原財經法學,第46期,頁45-90,2021年6月。
- [3] 王怡蘋,契約自由與著作人格權之保護,輔仁法學,第51期,頁1-52,2016年6月。
責任編輯:盧頎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