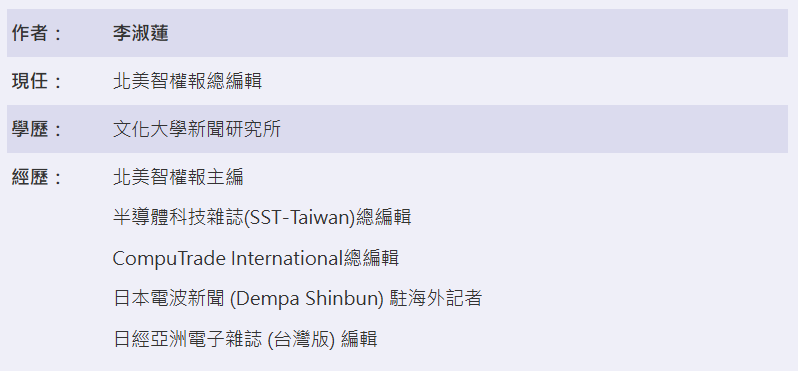2024年起,美中貿易局勢再度緊繃。面對川普式關稅政策捲土重來,台灣經濟的神經再次被牽動。台灣中小企業是否足以應對這場重壓?又將如何因應全球貿易規則重組所引發的深層變動?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黃勢璋日前於「川普關稅風暴 智庫視角 x 政策對應」研討會的專題演講中提出深刻見解,點出中小企業的結構本質、產業挑戰與未來機會。本文將整理與延伸其觀點,深入剖析台灣中小企業於變局中的角色與韌性。
中小企業是經濟結構的主體,不僅是輔助角色
根據中經院中小企業研究團隊的調查統計,台灣全國169萬家登記企業中,98.8%為中小企業,創造了台灣近八成的就業機會,且貢獻過半的銷售與內需總值。長期以來,儘管社會目光往往聚焦於台積電等科技巨頭,但中小企業在支撐整體經濟、維繫地方就業與社會穩定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實難以取代。
特別是在內需市場部分,2023年數據顯示,中小企業貢獻了高達61%的內銷金額,即便在資本規模與技術層次上無法與大企業比肩,但其「量」與「廣度」形成了龐大的基礎經濟結構,是實質上穩定台灣社會經濟的重要支柱。
高科技貿易戰外溢效應正重擊傳統製造業
在台灣,中小企業集中於傳統產業領域,如金屬製品、機械設備與零組件等製造業,而這些正是美中貿易衝突波及最深的環節。黃勢璋指出,金屬製品製造業占中小企業出口比重高達27%,而機械設備製造業則緊隨其後。這些產業本身出口導向性高,又多以中間材、零組件形式供應全球製造鏈,在全球關稅升高與市場收縮之下,最容易受傷。
特別是當中國商品出口美國受阻後,轉向其他市場傾銷的「溢出效應」可能使得台灣中小企業在第三地市場的競爭力進一步削弱。再者,原物料價格上漲、運輸成本波動與訂單轉單效應,都讓中小企業在供應鏈中處於更為被動的地位。
結構性挑戰更加劇危機反應力的不足
除了外部貿易風險,台灣中小企業還面臨長期結構性挑戰,包括接班困境、數位與綠色轉型門檻高、人力資源流失與市場拓展能力不足。黃勢璋特別指出,台灣約七成中小企業為家族經營模式,代際傳承缺乏制度化,容易陷入「一代企業、二代消耗、三代結束」的危機循環。
此外,數位化與綠色能源轉型雖是當前趨勢,但資源限制使得多數中小企業難以自行投入技術改造或符合國際環保標準;一旦國際買家將碳足跡、ESG納入採購標準,中小企業若無法即時跟上,就可能被排除於全球供應鏈之外。
決策應以「小國戰略」為指導,尋找務實突圍路徑
面對不穩定且高度政治化的貿易環境,黃勢璋強調,台灣身為小國,應採取「順勢而為」的彈性策略。不是正面對抗,而是審時度勢、掌握邊緣優勢。透過強化與美國、日本、歐洲等高附加價值市場的技術合作,讓中小企業能在更高層級的製造與服務鏈條中找到立足點。
他舉例,像台灣在汽車零組件售後市場(Aftermarket)就有明顯的國際競爭力,一些廠商即便在高關稅環境中仍維持接單水準,可見中小企業若能找到定位、強化差異化能力,仍有突圍之道。
從政策面到實務面:中小企業轉型的四個支點
黃勢璋建議,中小企業未來的發展必須倚靠以下四個政策支撐點來強化自身體質:
首先是資金援助機制的強化。中小企業資金來源匱乏,政府應進一步擴大信用保證與貸款利率優惠,特別是針對綠色轉型與數位轉型相關投資項目。
其次是產學研平台的再造與落地。政府應結合高校與研究機構,建立地區型轉型協助據點,讓科技不再停留在研究室中,而能貼近企業實際所需。
第三為推動區域聯合製造。中小企業難以獨力面對全球化的營運成本與市場風險,可鼓勵產業集群進行跨國協作,例如在新南向國家設置共同生產基地,強化在地供應鏈韌性。
最後則是導入差異化市場與品牌策略。台灣中小企業應跳脫OEM思維,積極投入設計、品牌經營與通路建構,從附加價值低的生產端,走向高利潤的市場前端。
結語:不確定年代中的中小企業智慧
川普式關稅政策不是第一波,也不會是最後一波。對中小企業而言,真正的挑戰不僅來自於政策變動本身,而是能否快速回應、持續轉型,以及在變動中建立自身的辨識度與價值。
如黃勢璋所說:「中小企業的本質就是彈性與韌性,如果這兩項特質無法轉化為實質競爭力,那就只是被動地等待風暴。」在這場全球經濟格局重組的浪潮中,唯有轉動自身齒輪,台灣中小企業方能在夾縫中求生存,甚至找到壯大的可能。